耐克回到起跑线
撰文| 文烨豪
编辑| 吴先之
2004年雅典奥运,刘翔以12秒91打破奥运纪录,把一枚田径金牌带回了一个此前并不以短跑著称的国家。
比赛结束不久,一支广告迅速上线:起跑、腾空、跨栏、冲线,被剪辑成凌厉的蒙太奇,配以设问:“亚洲人缺乏爆发力?缺乏必胜的气势?”——不等观众回答,刘翔已然冲线庆祝,“你能比你快” 的广告语随之浮现。
这支广告,属于耐克。
彼时的耐克,是少数能听懂中国,亦理解一个正在苏醒的国家,对“第一”的渴望与自豪的品牌。

然而,二十年后,这种连接逐渐松动——从渠道体系,到产品叙事,再到品牌形象,耐克慢慢困在自己编织的网中,曾经滚烫的品牌叙事,变得遥远且模糊。
财报显示,最新财季,耐克大中华区营收同比下滑21%,降至14.8亿美元,已连续多个季度走低。电商业务下滑 31%,批发渠道下滑 24%,自营门店亦下降 6%。这个曾经的“优等生”,成绩正迅速滑坡。
数字只是结果,不是原因。真正的裂痕,是那种渐渐消退的,品牌与时代之间的“共谋感”。
而当下的耐克,正在积极自救:艾略特·希尔回归、Win Now战略启动、产品更专业、渠道更包容、品牌精神亦试图回到原点。
一切都像是教科书式的应对,但问题似乎并不在“对”与“错”本身。
为了热钱,卖掉信仰
在中国市场的多数年份里,耐克几乎不需要主动奔跑。
彼时,尚处品牌力主导市场的时代,耐克几乎是一家“躺赢”的品牌——连续二十个季度的双位数增长让“竞争”这个词显得多余,没有敌手,只有臣服。
但任何长周期的繁荣,往往都藏着迟来的问题。赢得够久,难免会高估自身的自洽能力,即便出现裂缝,也容易被解释为“纹理”,直到市场哗然收水,惯性失效,问题才一并涌现。
炒鞋,是最早传出的异响。
2019年前后,球鞋市场骤然升温,迅速被二级市场资本化。
社区的语言也随之更换,球感、脚感逐渐被边缘,取而代之的是涨幅、货量、编号、补货节奏——一双鞋被当作股票,反复拆解、追踪、博弈。
品牌制造稀缺,转售缔造溢价,两者形成闭环。短期来看,此番打法相当奏效,诸多潮流品牌、潮玩玩家,都曾照此运作。
对品牌而言,它更适合制造声浪,难以承载增长。鞋市也好,潮玩也罢,本质上一种脆弱的繁荣——不创造价值,只加速透支品牌的未来预期。也因此,真正清醒的玩家,往往在热度见顶前抽身,及时收回对市场的控制权。
偏偏那时的耐克,正好把方向盘交给了一个只顾着踩油门的人。
2020年,约翰·多纳霍出任耐克CEO。

彼时,AI尚在酝酿,数字化转型仍是企业叙事的主线。此番语境下,咨询行业出身的多纳霍非但没有祛魅,反而自带光环。
作为职业经理人,其承担着“用先进方法论改造传统品牌”的期望与压力。而球鞋市场的爆发,恰好是难得的机会——可被整合、可被放大,更重要的是,可以立刻做出成绩。
而DTC(Direct to Consumer)模式,自然成为了最清晰、也最稳妥的路径。
全球语境下,DTC被视为顺理成章的效率改革:Nike App、自营门店、SNKRS社区……一整套新零售阵列迅速铺开,几乎满足了组织内部对“数字化成果”的全部期待。
对外,它讲的是“更贴近消费者”;对内,则更像是对“中间商赚差价”的清算——剥离代理、压缩空间,把流量和利润统一纳入品牌自己的闭环里。
与此同时,DTC改革让耐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主导权。
传统分销体系下,货品一出库,品牌便随之退场,在自有渠道中,耐克则能掌控节奏与流向;而用户的每一次浏览、预约、抽签、支付数据,亦将被收录、分析——一款鞋是否能火,不再依赖终端滞后的售罄或排队来验证,而是由系统前置感知。
基于此,鞋市狂热中,耐克虽未亲自下场,却始终在场,并在幕后主导了筹码的分配:限量制造稀缺,情绪升温后择机补货,节奏总比市场慢半步,却永远踩在利润点上——不留口实,也从不空手而归。
数据显示,2019年至2022年,DTC的营收比重从32%提至43%,SNKRS与Nike App在部分区域市场甚至一度取代门店,成为发售主渠道。
一切似乎都在提效,改革也推进得异常顺利。殊不知,高歌猛进的表象下,正悄然酝酿着危机。
在《鞋狗》中,耐克创始人菲尔·奈特曾给“鞋狗(Shoe Dog)”留下过近乎私人化的定义:那些全身心投入制鞋、卖鞋、买鞋或设计鞋的人。这个词听上去带点自嘲,却始终保留一丝敬意——只有真正爱过鞋的人,才配得上这个称呼。
约翰·多纳霍显然不是“鞋狗”。
他对鞋没有执念,对“运动”也没有执念。他的世界建立在指标之上,组织、渠道、业绩、KPI才是他最熟悉的语言。
因此,自他上任起,耐克越来越像一家“公司”,而不像一个“品牌”——标准化与业绩优先的逻辑,像网一样收拢着这家企业曾经的野性与多样性。

最典型的,是组织重构。
约翰·多纳霍主导下,曾经围绕“篮球”“跑步”“训练”等构建的架构,被“男/女/儿童”的三大类别所取代。这看似更贴近用户结构,实则是品牌精神的消解:品牌不再以运动为内核展开叙事,而转向清晰、需求扁平的消费单元——耐克与运动的关系,也因此变得抽象、遥远。
这种“效率优先”的逻辑,在中国市场的另一端,撕裂得更为剧烈。
无数存在于中国灰度地带的中小代理商,本就在此前品牌集中化的趋势中迷惘、淡出,DTC改革提速后,尾部渠道几乎全线沉寂。而像滔搏这样的头部分销商,也开始感受到压力——热门款、限量款的配额愈发稀薄,渠道价差逐渐失去腾挪空间。
问题在于,无论是滔搏这样扎根低线城市的中间层,还是那些与体校、体委长期共生的老分销商,虽在“效率”视角下被视作冗余,却是品牌触达社会肌理的“毛细血管”。而挥动着直销重拳的耐克,好似把品牌从更广域的消费土壤中拔了出来。
最终,泡沫在膨胀中破裂,耐克的精神肌理亦被掏空。以至于热潮退去后,品牌开始遭遇断层:一线城市的门店陷入库存与打折的恶性循环;下沉市场则因触点坍缩,逐渐失联。
盛世之下,品牌精神止于沉默。
灵魂的重量
很多时候,当一家企业步入动荡周期,权力的重构往往会先于战略选择浮出水面。
尤其当组织需要对抗阻力、推动争议决策——比如激进转型、变革渠道、削弱既有盟友体系时,往往不会由真正的“核心”来出面,而是将任务交由“合适”的人,比如从外部引入职业经理人,或将恰好处在边缘位置的高管推向台前。
后者看似站在聚光灯下,实则身处风暴中心,既是改革的执行者,也是后果的“背锅人”——以“个体”之名,完成组织层面的泄压与兑责。
因此,不能将一切后果粗暴归因于某位CEO的判断,毕竟很多所谓的选择,是组织惯性下的必然。
以大中华区为例,炒鞋热退潮,并不等于需求坍塌,而是品牌回归正常的生长节奏。可此后几年,耐克却未能重拾增长,自然有着更深的原因。
据悉,耐克采用典型的矩阵式结构,全球主导产品与品牌,区域负责渠道与执行。大中华区虽设总部,却不免束于“中央集权”,难以展开独立的战略定调与叙事框架,甚至就连核心的鞋款设计,亦集中于俄勒冈。
扩张阶段,它是一种秩序;收缩阶段,则成了拖拽——越是追求一致,越容易压制局部的反应力。
《重新定义公司》中,施密特指出,组织效率并不取决于结构多坚固,而在于反馈机制的灵敏。“Speed matters”——速度远比层级体量更关键。而耐克过去有完整、厚重的组织体系,却鲜有应对突发变化与局部异动的“敏感神经”。
这点,在某次国内舆论风暴中,暴露得尤为彻底。面对群情激愤的大众情绪,耐克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迟钝——回应滞后、表态迟缓、措辞僵化。
表面看,这是公关失控;深层看,则透着耐克全球架构的长期积弊——本意是为了控制复杂性,但最终却封闭了对复杂性的感受。
后果可谓相当严重,多年铺设的KOL体系哑火,明星代言相继切割,用户心智塌缩……一个全球品牌的感知力,在它最需要共情的时刻,彻底坍塌。
随着业绩连季承压,组织文化持续钝化,耐克终于意识到,问题不再是“鞋卖不动”这么简单。
2024年,它开始向内回望。
这一次,耐克没有再用“市场疲软”做挡箭牌,也不再指望靠单点产品或营销奇袭挽回局面,而是直接对权力轴心动刀。
修复,从最顶层开始。
创始人菲尔·奈特重新现身,召回老将艾略特·希尔,并提出Win Now战略——这位从门店销售一路爬升至全球品牌总裁的“鞋狗”,被寄望于唤回那个旧日耐克的精神质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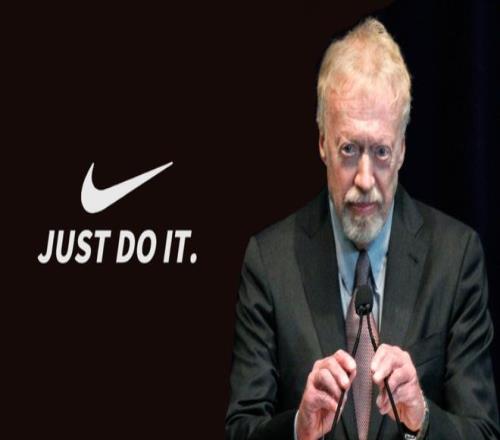
相比偏好指标与Excel的多纳霍,希尔显然更擅长处理那些无法量化的部分——品牌气质、文化肌理、组织叙事等层面的“软组织撕裂”。
比如在品牌张力迅速消退的国内市场,耐克启动了本地创意中心 Icon Studios,放权本地内容团队,尝试打破过去“全球叙事、区域执行”的旧秩序。
几乎在同一时间,耐克中国区也完成了一次关键性的人事更替:外籍高管退场,由来自中国本土、在耐克体系中成长二十年的董炜担任大中华区董事长兼CEO。
这一系列操作,似乎释放着某种信号——一贯强势的耐克,似乎在区域治理上释放出更大的弹性。尽管这未必意味着结构性松动已然发生,但至少表明,耐克正在重新理解“本地适应性”的组织逻辑。
更深层的变化,也潜藏其中。
从倚重“通才”,到相信从内部爬升、亲历品牌每一寸演化的“内生者”,耐克似乎终于明白——想要救品牌于水深火热,需要懂它、爱它、扎根于它的人。
往回走,也往前去
人与组织的问题,归于内部,尚可凭组织意志纠偏;外部挑战则客观存在,不因组织意志而转移。脱离泥沼,再植土壤,才是更漫长、更现实的部分。
整体来看,Win Now 战略像是一种回拢:重拾运动文化叙事、修补渠道关系,对过往的激进打法进行拨乱反正。
其中很多动作,本质上是“还债”。
比如产品线的收放。以Dunk为例,2019到2022年间,其推出了两百多个配色,几乎月月上新,沦为“调色盘”。而大水漫灌之下,Dunk原本的街头、反叛气质被透支、消解,最终淹没在库存之中。
突然走红的演员,往往需要在热度顶峰及时抽身,才能避免被角色定义一生。而耐克现阶段正将其三大经典鞋款(Air Jordan 1、Air Force 1、Dunk系列)“从主角位撤出”,以修复产品叙事的密度与梯度。

与此同时,耐克开始回头,重返那个曾最擅长的场域:专业——技术鞋款回归中心,也更愿意将预算砸向技术。
对运动品牌而言,追求专业自然是对第一性原理的回归。但也正因如此,“专业”本身,很难成为“选择”——当所有人都站在同一块基石上,分野,注定只能来自别处。
事实上,过去几年间,国内用户偏好正悄然转移——从追求胜负、速度、极限,转向了呼吸、松弛与生活方式。而讲了几十年“赢”的耐克,却几乎缺席了这场近些年最温和、也最彻底的运动消费迁徙。
其实,耐克并不是没有户外基因。1989年,其就曾推出名为 ACG(All Conditions Gear)的专业产品线。但此后的三十多年里,ACG几经沉浮,反复被提起,又反复被遗忘,从未真正扎下根来。
值得一提的是,2015年前后,耐克曾请来潮流“黑武士”Errolson Hugh,为ACG改头换面。他用极简、先锋、机能等语言,为这一老牌支线注入了时尚血液。而被改造后的ACG,一度击中了“潮流圈”的审美,但也逐渐丢掉了“为户外而生”的初心。
最终,耐克留在城市,消费者却已经上了山。而安踏,则悄悄登上了神坛。
而现在,四处寻路的耐克,也终于开始“朝花夕拾”。ACG全球CEO的职位,亦伴随着前述组织架构调整,一并交到了董炜手中。
将一个全球子品牌的控制权,交给一位区域市场负责人,背后自然有着更深的意味——此刻的耐克,或许并不那么需要户外,但却真的不能再失去中国。
归根结底,从人到组织,再到打法,耐克做着品牌该做的一切。只是,有些连接尚可失而复得,有些叙事则永远定格在当年冲线的那一帧画面中。好在,耐克重新回到了路上。
这一程,或许不是为了追赶谁,而是为了找回那个尚未走远的自己。
慢慢地,往回走,也往前去。
微信号|TMTweb
公众号|光子星球
别忘了扫码关注我们!
